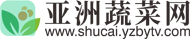作者:嘉 宏
音乐有着穿透一切的魔力。田青是国内研究民间音乐和宗教音乐的专家,兼具深厚的理论素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国人的音乐》一书是他关于中国音乐史方面的最新著作。作者在书中梳理了中国音乐的源流和演变趋势,化繁为简讲述了乐器与器乐、民歌与声乐、新音乐的发展历程。《中国人的音乐》是一本讲中国传统音乐的、具有艺术普及功能的书,也是一本通过中华传统音乐来讲中国和中国人的书。
敦煌壁画《观无量寿经变》表现了唐朝宫廷燕乐的表演情形
 (资料图)
(资料图)
《中国人的音乐》田青 著中信出版集团
出土于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的贾湖骨笛,距今7800—9000年。
音乐中的“和”文化
“假如让我只用一个字来概括中国音乐,那就是‘和’。”著名音乐学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名誉所长田青认为,这个“和”字,不但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最高体现,也是中国人和中国音乐的最终追求。
早在公元前522年,政治家晏子就以音乐为例,生动、准确地阐明了“和”的本质,指出音乐有不同的“清浊、小大、短长、疾徐、哀乐、刚柔”。假如音乐只是相同声音的不断重复,那“谁能听之”?千百年来,中国人将从音乐中悟出的“和而不同”的道理上升为哲学,落实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田青指出,人类几乎所有艺术都源于对大自然的模仿。比如人们在绘画与雕塑时描摹的对象是大自然中的一切,赤橙黄绿的颜色与各种形体也都是自然存在的。但音乐略有不同,虽然自然界存在着风声、雨声、瀑布声、鸟鸣声,但这些都只是噪声,不是音声。中国人更是从先秦时就将人耳所闻分为三个层次——“声”“音”“乐”,中国最早的一部音乐理论著作《礼记·乐记》中说:“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唯君子为能知乐。”意思是禽兽只能听懂同类之间的“声”,普通人只能懂得由“音”构成的语言,只有掌握了文明密码的君子,才懂得音乐。
中国的音乐史可以追溯到八九千年前。1987年,河南省舞阳县贾湖遗址出土了著名的贾湖骨笛,它有7孔,由仙鹤的尺骨做成,可吹奏七声音阶的现代乐曲,且音色优
美。这表明我们的祖先在8000多年前就已经创造发明了一种完备的管乐器。
在中国文化里,音乐绝非可有可无的附属品。以“孔孟老庄”为代表的先秦诸子都对音乐有着清晰、深刻的论断。最典型的要数孔子,他不但认为人格养成的途径是“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把音乐文化视为最高修养,而且他就是位音乐家,会弹琴、唱歌,并且“无故不撤琴瑟”。
一个神奇的现象是,我们的祖先认为,把“礼”和“乐”结合在一起,可以使社会安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早期中华文明更是世界唯一的礼乐文明。田青赞同荀子“乐和同,礼别异”的观点,认为“礼”使人和人有区别,有尊卑,有秩序;“乐”则是通过人类能够共同理解和欣赏的艺术形式,找到人们的共同点,让人和人之间有关爱,有亲情,从而达到“和”的境地。“我们的祖先和现代社会的人不同,他们在音乐中追求的,不是发泄,不是放纵,而是平静与和谐,是心与身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人与大自然、万物、天地的和谐。”
关于音律的起源,《吕氏春秋》中有这样一个传说:黄帝命令臣子伶伦制定乐律,伶伦来到昆仑山,听到凤叫了六声,凰叫了六声。于是,伶伦就在山下的“嶰溪之谷”用竹子做了十二根确定音高标准的“律管”,模仿凤凰的鸣叫。这就是黄钟、大吕、太簇等十二律的来历。其中,“黄钟”是中国音乐的标准音,十二律则成为中国音乐千百年来的基础和规制。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政权建立之后要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制礼作乐”。其中就包括要制定黄钟的音高标准。不仅如此,吹出黄钟音的管子,还是制定国家度量衡的标准:以黄钟律管长“九寸”来定“尺”的长度,这是“度”;将黄钟律管里装满黍,倒出来后称量,其体积和重量就是“量”和“衡”的标准。可见古代的中国人多么重视音乐。
从“雅乐”到“燕乐”
1978年,湖北省随县(今随州)擂鼓墩发现了一座古墓,让现代人一睹春秋时期礼乐文明的辉煌。这座古墓的墓主叫曾侯乙,是战国时期曾国的君主,下葬于楚惠王五十六年(公元前433年)或稍晚。该墓共出土文物1万多件,光乐器便有125件,包括极难保存的竹制和木制乐器笙、鼓、排箫、篪、五弦琴、十弦琴、二十五弦瑟。其中最宝贵的发现,是一套共有65件的青铜编钟,即“曾侯乙编钟”。
编钟出土时分三层八组,挂满了墓室的整整三面墙,正符合《周礼》中“诸侯轩悬”的规定。田青指出,这套编钟除了精美庞大,还有几个“世界之最”。第一,这套编钟音色纯正优美,高音清朗,中音明澈,低音浑厚深沉,而且每件甬钟可以敲击出两个大、小三度的和音来,改写了此前“中国音乐就是单声音乐”的看法。第二,这套编钟总音域达五个半八度,其音列与现代的C大调相同,可顺利地“旋宫转调”,甚至可以用来演奏巴赫或者贝多芬的音乐作品,改写了“中国音乐就是五声音阶”的认知。第三,在这套编钟的钟体上,铸着三千七百多字的钟铭,这篇音律学“论文”详细记载了各国不同律名、阶名、变化音名之间的对应关系,篇幅之多、含义之深,皆为世所罕见。
曾侯乙墓出土的编钟、编磬,加上建鼓、琴、瑟、篪、排箫等乐器组成的乐队,就是先秦盛行的“雅乐”演奏阵容。春秋之际礼崩乐坏,雅乐衰微,琴、瑟、篪、箫等乐器流入民间。西汉张骞凿空之后,大量外域乐器、乐曲流入中原,成为上至皇帝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共同追捧的“流行音乐”。隋唐时期,逐渐形成了又一种音乐形态:燕乐。
燕乐也称“宴乐”,泛指当时在宫廷或贵族的宴会上所演唱、演奏的音乐,其中包括独唱、独奏、合奏,大型歌舞曲及歌舞戏、杂技等。而最有影响和艺术价值的,则是被称为“大曲”。这是一种含有多种艺术形式的大型歌舞曲,一般有三大段。
燕乐大曲中最著名的有《秦王破阵乐》和《霓裳羽衣曲》。前者规模宏大,声名远播域外。《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载,印度的戒日王曾问玄奘《秦王破阵乐》的来历。日本遣唐使也曾将此曲带回日本,至今在日本仍保存有名为《秦王破阵乐》的五弦琵琶谱、琵琶谱、筝谱、筚篥谱、笛谱等多种乐谱。《霓裳羽衣曲》则是燕乐大曲发展到顶峰的产物,它继承并发展了燕乐大曲成熟的表现方法,同时凝聚了包括李隆基、杨玉环在内的许多人的智慧。
燕乐是大唐繁荣昌盛的象征,也是当时世界上最高水平的音乐文化,曾给朝鲜半岛、日本、东南亚诸国以深远的影响。安史之乱后,乐工星散,这些音乐只能留存在诗人的记忆里。白居易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杜甫的《江南逢李龟年》等,不但记载了盛唐燕乐给诗人心灵带来的震撼,也记载了燕乐衰败后诗人的唏嘘哀叹。
民歌登上大雅堂
古人说“情动于中,故形于声”。当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让你激动,需要表达时,语言的局限性便成了障碍。语言表达不了,一边拍大腿一边大声嗟叹还不行,就只能唱了,正如一首山西民歌中唱的:“心中难活唱一声。”
歌的最初形态是民歌。田青直言,民歌是我们的爷爷奶奶唱过的歌,里面有祖先的喜怒哀乐,有民族、地域、家乡的历史和生活,有不尽的乡愁。千百年来,民歌在传唱中不断丰富、发展、传布,积淀在世世代代中国人的心灵深处,成为我们民族、地域的一个标志。比如《东方红》,就是随着中国革命的浪潮从陕北唱响全中国的一首升级版民歌。
《东方红》的曲调原为陕西、山西、内蒙古南部广泛流传的民歌曲调。被称为“黄河拐弯”的河套地区原本在文化上就属于一个系统,很多共生、共有的民歌风格相同或近似。其原始曲调演唱的陕北民歌歌词是“蓝格莹莹的天,飘来一疙瘩瘩云,刮风下雨响雷声,三哥哥今要出远门,呼儿嗨哟,你叫妹妹不放心”。在晋西北,也有一首相同曲调的民歌,歌词为:“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哼儿咳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抗日战争时期,此曲曾被改编成抗日歌曲:“骑白马,挎洋枪,三哥哥吃了八路军的粮,有心回家看姑娘,呼儿嗨哟,打日本就顾不上。”这就是被视为《东方红》前身的《骑白马》。1943年,陕西葭县(今佳县)农民歌手李有源依照《骑白马》的曲调,编写成一首《移民歌》。随后,延安文艺工作者将《移民歌》整理、删修并改名为《东方红》,于1944年在《解放日报》上发表。随着解放大军的南下,《东方红》迅速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
新中国成立后,作曲家李焕之将其编写为管弦乐队伴奏的大合唱。在专业作曲家的精心研磨下,这样一首民间小调华丽转身,成为新中国最具代表性的宏大颂歌。1964年,以《东方红》命名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上演,这台节目以国家的力量调动顶尖艺术家集体创作,有3000多名演员登台演出。在“序曲”中,《东方红》的旋律以恢宏浩大的音乐,配合中国古代乐舞的最高规格“八佾”舞,将“颂”这个在《诗经》时代便已出现的体裁发挥到极致。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编钟演奏的《东方红》曲调作为每天开始广播的“呼号”和标志性乐曲。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被命名为“东方红一号”,在围绕地球运行的浩渺太空向宇宙发射《东方红》旋律的电子信号,让这首来自中国西北偏远山乡的民歌,成为“遨游太空”的中国符号、中国声音。
这样充满传奇的歌曲还有许多。因乐可知心,因乐可知人。可以说,懂得了中国人的音乐,也就懂得了中国人,懂得了中国。(嘉宏)
(来源:齐鲁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