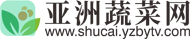【资料图】
【资料图】
巴尔扎克的银子(中篇小说)
文/李亚
我舅舅方程先生是个研究巴尔扎克的知名专家,要不是因为和太太闹离婚牵连了多年的精力,那他到现在出版的研究专著恐怕要比《人间喜剧》还要广阔。这场离婚事件好像狗吃糖稀拖拖拉拉了好长时间——现在的时间也像吃了假冒伪劣的仙丹一样消逝得飞快,一眨眼七八年。
当然了,现如今全世界到处都有漫长的离婚事件,从遥远的巴黎和伦敦,到附近的上海和北京,包括我们这个有着一条大河贯穿其间的小小城市,漫长的离婚事件好像雨季过后森林里的毒蘑菇一样肆意丛生。在宇宙中,在世界上,在我们这个小小城市里,不管离个婚要拖多久,也很少再有人为此心烦意乱,因为已经没有几个人会把这件如今在哪儿都是稀松平常的小事放在心上。我舅舅脸颊白皙、鼻梁高挺、一对卧蚕眉,他躺在院子里的竹制躺椅上,双手扬起抚摸着油罐子一样光滑的秃顶,眯缝着一双丹凤眼微微奸笑着说,巴尔扎克自从1832年2月底接到韩斯卡夫人的第一封信,到1850年3月初他们在基辅办好结婚证书,也就是说,仅仅结个婚巴尔扎克这个骚胖子就花了整整18年时间,切,我离个婚花上七八年又算个什么!
在穿城而过的大河北岸,这个院子有些年头了,听我舅舅说这座宅院是他祖辈留下的遗产。他太爷爷和爷爷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父亲又是个什么了不起的人物,等等。到底有什么了不起的呀,非得挂在嘴边三番五次地叨叨,好像我不知道那些早就跌入历史尘埃的腐朽事情一样。而且,我也早就习惯了我舅舅的鬼话连篇,说起瞎话眼也不眨,即便从来没有发生、在这个世界上也绝对不会发生的事情要是让我舅舅说起来就好像正在你眼前发生着这件事情。其实, 只要试想一下就知道了:一个人要是大半辈子疯疯癫癫研究巴尔扎克,那他嘴里还能有几句真话可信嘛!更何况像我舅舅这么一个恨不得把自己的灵魂与肉体都和巴尔扎克融成一坨的教授先生。院子里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树,花开季节早已过去,微风轻拂树枝摇曳,斑驳的阳光照得我舅舅睁不开眼睛,空气里残存的桂花香就像根羽毛一样飞徊着拂拭他的鼻翼,他感到鼻腔内黏膜受到刺激,像食肉动物嗅到血腥气息一样他一连哼哧了一二十下鼻子。我舅舅鼻梁高挺,眼神深邃,宛如古希腊石雕人像……当然了,他年轻时的这般英俊相貌如今已躺尸在他的影集里了。现在,我的教授舅舅油性头发谢顶严重,几乎算得上半个明晃晃的秃头了,加之随着年龄增长人人难以避免的生理变化,他那双丹凤眼下边还涌上来小小的两泡眼袋,好像狂妄的麦粒肿不甘心地潜伏在那儿等待时机,尤其在魏武广场观看那群粗胳膊粗腿线条彻底消失了的大妈和奶奶们跳舞他微微坏笑时,两粒囊肿般的眼袋突然增大,活像青蛙鸣叫时鼓起的两个气囊。还有,我舅舅原本清澈深邃的眼神自从离婚事件开始也逐渐变得暧昧和茫然,高挺的鼻梁也因皮肤起皱生满斑点而显得有些鬼气、有些狰狞。当然了,这些算不得什么,这些变化一点也没有影响我舅舅的昂扬心态。我们这个小小城市以聚集和流通中草药闻名世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药贩子,因此我有闲有钱又经常无聊,所以隔三差五请我舅舅这颗孤独的光头吃吃喝喝,顺便听他讲有关巴尔扎克的无厘头趣事。我最爱请我舅舅到“水中央”大排档吃刚捕的刀鱼。这种鱼自古以来就是我们这个小城的特产名吃,尤其在春末夏初之际肉质异常鲜美。我舅舅不仅喜欢吃当鲜的刀鱼,他还喜欢那个给他上刀鱼的服务员小姑娘粉妮。粉妮是个混血儿,她的眼珠子蓝莹莹的好似波斯猫眼。我舅舅把粉妮叫作波莉娜,每次刚坐下就会昂着脖子大声呼唤:波莉娜,来杯扎啤!波莉娜,来份刀鱼呀!被他唤作波莉娜的粉妮就会快速把一扎啤酒和一份刀鱼给他端上来,然后,咬着下唇,蓝眼睛好像意味深长地给我舅舅眨一下再眨一下,然后带着几分嗔怪的意味扭着细长的腰肢走掉了。我舅舅很喜欢粉妮这副怪怪的样子。我舅舅还喜欢到“庄稼地”餐馆吃刚宰的地锅鸡,因为除了地锅鸡之外他还特别喜欢那个丰腴的服务员苏红,我们每次一坐下,丰腴的苏红就会拿着菜单快步走过来站在我舅舅腿边请他点菜。苏红不是本地人,她好像是苏北的还是陕北的也许是湖北川北的我也搞不清楚,我舅舅也搞不清楚,但我们都知道她36岁了。苏红丰腴白皙,一搭话就笑,两片厚嘴唇一笑显得特别性感。我舅舅特别喜欢点完菜之后她说的那句话:哥哥稍等,马上就妥了!苏红把“妥”字说成“脱”字,这个看似微不足道的口音小差异每次都让我舅舅特别亢奋。总之,不管吃刀鱼还是吃地锅鸡,他老人家都是兴奋地大吃大喝大声说笑。我舅舅根本不在意邻座男女食客装模作样乜斜过来的目光充满惊讶和厌憎,他照旧大声宣称在这一点上他比巴尔扎克厉害多了,别说巴尔扎克还没到他这个年龄就翘脚去那边了,那个骚胖子年轻时不太行,从乔治·桑给她的小情人桑多的书信和本人的自传里都可以推测出巴尔扎克年轻时就不太行。我舅舅那光秃秃的脑袋里不仅装满了巴尔扎克的趣事,还经常阵发性地突如其来生出一些莫名其妙的想法和念头。就像,他有两三次严肃地要求我在某些场合下尤其是在漂亮女人多的场合一定要称呼他方教授或者方先生,我一直都没有弄清楚到底为什么,因为我从小到大一直和我舅舅耳鬓厮磨就像多年父子赛兄弟一样,不管是潜意识里还是在实际生活中,早就没有了甥舅之分。哦,但有一点我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我舅舅方程先生确实是城南那所不怎么地的大学中文系教授。
(节选自2023年第3期《湘江文艺》中篇小说《巴尔扎克的银子》)